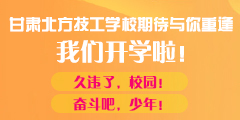|
对许多来北京打拼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大学生求职公寓”里的一张床铺可能是他们开始的地方。 这是“专门为来北京求职、在京工作的大学生提供住宿的家庭式公寓,地处繁华地带,交通便利”。一家大学生求职公寓的官方网站上这样介绍。这类求职公寓大部分由商品房改造而成,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能放下20多张上下铺,还有的隔断出租。 求职公寓集中在中关村、建国门、崇文门和双井地铁站这些地标建筑附近的小区里,尤以双井地铁站附近最为密集,仅百环家园、九龙花园等小区周边,就有50多家。 公寓最大的优势是价格,月租400~900元不等。部分也以天计价,每个床位最低的每日15元,最高的40元,有女生公寓、男生公寓和混住公寓。对于尚在实习或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很难在北京找到比这更便宜的宿舍了。据前述公寓的官网介绍,该公寓已接待了近5000人。 100平方米的公寓住20个人,阳台上也摆着一张床 考研失利后,毕业于徐州医学院的赵蔚在网上找到一份房产中介的工作,只身一人来到北京。第二天,经同事介绍,她住进了东二环附近某小区的求职公寓。 赵蔚上一次来北京是大二时来旅游。那时她觉得北京“又大又好”。到北京工作后,她总是觉得“新鲜有冲劲”。每天早上8点左右,赵蔚和她的同事出门步行一条街的距离,便可到达上班的地点。 求职公寓所在的小区环境不错,干净卫生。每天清晨或傍晚,都会有人在楼下的园子里锻炼身体。小区4个门都有保安把守,门口贴着“禁止园区穿越”告示。 小区内主要为16层高的电梯商品房,出入须打开密码锁。赵蔚所住的求职公寓就在其中一幢里。住在求职公寓里的租户会刻意保持与其他住户的距离,“碰到了也不会打招呼,就怕被别人知道是群租,然后举报我们”。 公寓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102平方米。赵蔚住在卫生间旁的4人间,内有两张上下铺,显得拥挤不堪。向着厨房的是一个6人间,目前住了5个女生。最宽敞明亮的是客厅,摆了5张上下铺,共10张床,现在住了8个人。 小区周边商圈环绕,且离地铁站公交站都很近,作为房地产中介,赵蔚深知附近的房价之高。“我住的这套公寓七八百万元,”赵蔚说,“每个月800元的房租,其实还是很划算的。” 赵蔚所在的4人间里目前住了3个人,她、一位50岁左右的外地阿姨,还有正在北京实习的张羽。屋里除了床,还摆着一个五层的置物架,窗边、床底下摞着一个个大纸箱,“大家都用它来放东西”。唯一的装饰是窗户旁挂着的一盆吊兰,同屋的阿姨会定期给它浇水。 屋里放着一个公用的塑料凳子,地板早已由原本的黄色褪为褐色。每天早晚会有一个保洁来公寓清理卫生,但4人间的阿姨并不愿意保洁进这个屋里,“那公用的拖把多脏啊,何况她还要打扫那么多家,哪能打扫干净,我倒宁愿自己打扫。” 这里的床铺都是典型的1.2米宽的宿舍上下铺,床头床尾都挂满了衣服,“没办法,衣服太多了,又没有柜子,只能找地方挂起来了”。张羽将洗后的衣服也挂在床沿。她说:“阳台每天都挂满了衣服,我只能把衣服都挂在这里,根本晒不到太阳。” 赵蔚住上铺,她常在床上吃零食,还在床头挂了一个塑料袋,“休息的时候就不想下床,垃圾就都扔这了”。 相对于客厅的上铺每月700元、下铺每月750元,4人间和6人间要贵些:上铺月租800元,下铺850元。“如果一次交三个月的房租,可以让房东给你优惠,大概能抹去150块。” 尽管离单位近,不用起特别早,但赵蔚每天工作12个小时。有时为了帮客户过户,还得凌晨3点起床和同事骑自行车去房管局排队。 赵蔚的同事万琳住在求职公寓的客厅。她毕业于山西一所普通高校的会计专业,原本通过考研大关的她有读研究生的机会,当学校研究生招生办给她打来复试通知的电话时,“因为家里连1万元的学费都拿不出来”,万琳最终还是选择了回绝。“家里人根本不知道我能上研究生,我也不想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就算读了研究生,也还是要出来步入社会的”。 放弃读研后,万琳开始给各大单位投递简历。她最想去的是太原某家企业,“在那里可以从事我的专业”,但对方告知必须要有出纳证才可应聘上岗,“即便我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人力资源等各种证书,也还是没用”。 距搬离学校宿舍还有10天的时候,万琳通过校园招聘找到了北京这份房产中介的工作。“一开始也没想到自己会干房地产,”万琳说,“一方面是我的无奈,怕自己无处可去,另一方面也是想在北京‘挣快钱’。” 万琳买了一张学生票,兜里揣着300块钱上了火车,上车后却被乘务员告知不支持该区间,要求她补90元票价。“我真不愿意把钱给她,给了她我在北京吃什么住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了。”万琳说。当时,在同一节车厢里,一位站在列车过道上妇女因被要求补票哭,“看见她哭我也哭了”,或许是于心不忍,最后乘务员只让万琳补了30元票价。 万琳比赵蔚早来北京一个月,来北京的第一天,同事帮她在这个小区找了一间求职公寓,“我挑最便宜700元床位住,但这个价格还是比我预想的高”,她向同事借钱交了第一个月的房租。 万琳和赵蔚难得休息,就连每周一天的休息日也可能接到突发任务。“我对现在很满足,每天有事做就行,我不想让自己太碌碌无为了。”万琳说。 来北京做调研的王蕊和李倩曾经在双井附近的一间求职公寓住过。那是一个两室一厅一厨一卫,一进门便可看到客厅两壁上下铺一个接一个整齐地摆放着;不到13平方米的房间,摆着3个上下铺;就连卫生间与厨房的过道里,也摆着一个上下铺。过道另一边,放着一个柜子,这是租客锁贵重东西的“保险柜”,每个人一小格,能放下一个书包。 “逼仄”,是她们进屋里想到的第一个词。在王蕊看来,最为夸张的是,阳台摆着一张单人床,单人床上方不到50厘米处则挂满了衣服。但这张床不常有人睡,王蕊来的第一天没有床位,就在那里睡了一晚,“有时候一个翻身就能够着上方的衣服。” 李倩的下铺是一个大学毕业后来北京已两年的女生,她在一家私人教育机构教英语。周末休息的时候,这个女生哪里也不去,打开电脑看视频,甚至吃饭都在床上。 住在这里的人生活里充满紧张 住这类公寓的有像赵蔚一样大学毕业后做着房产中介的工作,拿着刚入职3000元左右的工资;有大学毕业后来北京做导游、销售的,月薪2000元到1万元都有;还有在做投资的女生,每月工资轻松过万;还有领着每月1000元左右补贴的大学实习生。 有人上夜班,有人一大早起床赶地铁,“大家上班时间都错开了,所以显得也不是那么拥挤”。 那个做投资的女生是北京人,家住得远,平常谈生意都在这附近的商圈或办公楼里,干脆租了个铺位,偶尔赶不及的时候来住住。 许多求职公寓声称须查看大学毕业证才能办理入住,但事实上,登记身份证就够了,有的连租赁合同也不用签。 金丽住进某男女公寓的第一天,房东登记了她的身份证,和她签了合同,一张打印的A4纸,“上面写着房费押金和双方要遵守的一些规则”。 在这间公寓里,每天都有很多人进进出出,上下班的,看房子的。房东并不会太关心租客们的一举一动,唯一的条件是每月准时交房租。 赵蔚刚来的时候一次性交足了三个月的房租,三个月后,她开始每个月交一次。“最近经济有点拮据,每个月可能连3000元工资都领不到了。”赵蔚说,“而且谁知道哪天有什么情况呢。” 交房租的方式很新潮——微信转账。房东只有在催房租的时候才会偶尔过来一两趟,“她一般都不来这里,还有别的生意要做。”4人间的阿姨说。在这住了两年的李姑娘插话,房东是东北人,以前有三套公寓出租,现在只剩两套。“还有一套是大房东收回去了,不租了。” 群租的生活总有很多不便,比如赵蔚和她的室友常抱怨房间离卫生间太近,“睡觉、起床都会听到水哗哗的声音”。 相处也是件麻烦的事情,“那么多女生,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碰到特别合不来的就惨了。前几天刚住进来一个女生,当晚就和住在这的一个人吵架了。”原因是有人挪动了她刚搬进来的行李。 “再有就是蹲马桶的时候,”赵蔚说,“你刚坐上去,就有人进来催你了。” 晚上9点到10点是李倩认为的“最恐怖”的拥挤时间。一天晚上她们调研回来,想去卫生间洗手,却发现不到3平方米的卫生间已经站了5个人:一个人在内侧淋浴,一个人坐在马桶上和面前等待的一个女生聊天,还有两个女生占着洗手池。“二三十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实在是太恐怖了。”李倩说。 此外,使用公共物品时,“大家都不是很爱惜”。厨房的冰箱是所有租户共用,“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前几天还发现了蟑螂”。厨房里有一个3米长的灶台,上面摆满了厨房用品,其中有四个大小不一的电饭煲,两个锅。 太脏了,“不知道多少人住过了,厨房和厕所都很脏,以前的人留下来的盆盆罐罐都塞在那里,洗手间看起来黑乎乎的”。张羽显然比赵蔚更介意一些。 她甚至从来不用厕所和厨房,“我从来不坐上去,一般在单位上完厕所再回去。”“谁知道有什么传染病啊,”她也曾动过要自己做饭的念头,但还是“当即打住,也不可能购置锅碗瓢盆太多,划不来。” 混乱的公共设施偶尔会引发她们对于安全问题的担心。几乎每个上铺床边都搭着一个电插排,“这里的插排从来不拔下来。”赵蔚说。在卫生间,还摆着一个吹风机,天天接着电源,“那可是有水的地方啊,得多危险”。 住在这里的人生活也充满着紧张,几乎每栋求职公寓的大门后都贴着一张或几张字条,上面写的大多是禁止带外人进入,不随意开门。 “每当蹦出关于群租公寓的新闻我们都会很谨慎,”四人间的阿姨说,“但凡敲门都要问清楚是谁,就怕有人来查,我们就没有地方住了。”阿姨住在这里的近三年期间,她并没有遇到过查房的人。 有人把这里当成家,但对更多人来说只是一个过渡 很多人已经开始习惯这种生活,也许像官网上写的,“已经对这个‘家’产生了感情”。 赵蔚不忙的时候,也会和这里的同事一起聊天,用厨房做饭吃。 住在这里两年的李姑娘收入不错,但并不愿意搬走,“一个人住多不安全,这里好歹相互有个照应”。一位在北京工作了近10年的女生半年前住了进来,“一个人住太孤单了,一起住还有人说话”。 海南某高校毕业的朱瑶大部分时间都在找工作,每天一大早出门,到北京各大高校参加招聘会或者面试。面试后,朱瑶开始在网上搜寻各处的房子,“求职公寓只是我用来过渡的一个住所,主要还是想找单位附近的房子住”。她晚上10点多才回公寓,“快速收拾一下就上床,因为房东规定11点以后就关灯且不能洗澡”。 在北京面试了四、五家单位后,朱瑶进入了某企业实习,并搬离了求职公寓,“我比较喜欢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和很多人住在一起要照顾到大家,不能随心所欲”。 和她一起搬走的还有金丽。在顺利进入某媒体单位实习后,她总觉得“男女混住多多少少有些不方便”,在外另找了一个价格贵些的单间。 刚来求职公寓的时候,张羽还会和同公寓的人相互闲扯一下,“你哪儿来的啊,在北京找工作还是实习?”但实际上,直到她快搬走,“我连她们的名字都不太知道。” 她记得同屋的一个姐姐,做动漫设计的,工资有8000元,“我实在不明白她有钱了为什么还住在这种地方”。 离开公寓后,张羽偶然点开了那位的朋友圈,看到的却是一根拉黑的直线。“这直线就像我在北京的那段日子,一片空白的意思吧。”她有些遗憾,“虽然大家都很努力地在这个城市打拼、寻梦,不过我从来没有在这群年轻人身上看到‘我属于这个城市’的幸福感。” “他们当中很多人智商平平,家境平平,才气平平,这样的挣扎,我觉得就像给自己青春的一场名利谎言。”张羽说。 在北京打拼了4个月后,赵蔚现在觉得“心累”。每周与不同的客户见面,随时注意自己的言辞,“希望每一个客户都能签单”,而事与愿违,“社会就是和大学不一样”,即便客户不错,还得提防自己的同事,“勾心斗角的事情常有”。最让赵蔚气愤的是,有一次原本属于自己的业绩却都被领导判给一个同事,“我在经理面前哭了整整一天,他就看着我哭”。 万琳在北京常感觉“不知道该怎么融入这座城市”,“家乡人都说方言,亲切,在客户面前,说普通话的时候我偶尔会流露出一丝胆怯”。 她不喜欢现在的工作,辛苦,也没赚到钱,看不到未来。“在北京,很多事不是你努力就可以的。我也要为自己考虑,不能让我的青春就这样白白给了这座城市。” “现在觉得北京也就不过如此,除了机会多也就没其他的了。”赵蔚摇了摇头,“我想我在北京也不会长久待下去,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还是先好好做这份工作。” |
延伸阅读:
- ·毕业生遭遇更难就业季 自主创业或成新出路(2014-07-13)
- ·北京2000名初中毕业生将可直接升入高职(2015-03-12)
- ·李克强赠言创业大学生 赞厦大毕业生灵活就业(2015-04-24)
- ·致全省2015届初中毕业生的公开信(2015-04-28)
- ·重庆:要求各地做好高初中毕业生心理疏导工作(2015-05-14)

 护理专业
护理专业  多媒体制作
多媒体制作  铁路工程测量
铁路工程测量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铁道类专业专题
铁道类专业专题  幼儿教育专业
幼儿教育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