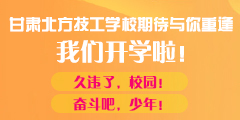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马文·沃尔夫冈教授做过一次经典的实证调查。在对1万名费城少年进行为期10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这些少年中有6%的人从小劣迹不断,而这6%的人所犯下的罪案占费城全年发案的50%。通过调查他认为,预防犯罪的核心,即是如何建立有效的法律防控机制,防止这6%的少年实施犯罪。
在我国,为减少未成年人犯罪,除刑罚手段之外,还设有工读学校与收容教养制度的双层防控机制。通过前者的特殊教育机制,不适宜在普通教育体制下的未成年人将获得有针对性的教育指导,从而达到对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正;后者的“教育、感化、挽救”措施,则试图让实施严重危害行为的未成年人能够改过自新。但就韦某的个案而言,这两道“安全门”却没能成功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创办工读学校,主要任务是对有严重不良行为和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转变。在实施之初,工读学校的入学带有强制性,但在1999年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实施之后就带上了自愿色彩。在自愿入学的背景下,全国工读学校急剧缩减,同时为补上经费亏空开始向就读学生收取一定甚至是高昂的费用。像韦某这样经济困难的家庭根本无法承担这笔费用,家长宁愿其在社会上放任自流,也不会考虑将其送入工读学校。就这样,第一层保障机制未能产生实际效果。
至于第二层防控机制,虽然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但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由于启动机制存在障碍而让效果大打折扣。比如,刑法规定收容教养启动条件为“必要的时候”,但这个规定过于模糊;再比如,刑法规定“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但“可以”意味着可酌情处理,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即使“必要的时候”已到,也不是必须收容教养。以韦某为例,他于2010年掐死男童后,所在的凤镇村村委会认为已到“必要的时候”,该由公安机关收容教养,但韦某最终并未被收容教养,仍自由出行,并最终导致2011年2月女童被伤害的悲剧发生。
让两道“安全门”真正发挥防控效用,一方面需要从立法上考虑赋予两者一定程度的强制性,以确保双层机制不再成为摆设,同时也应加大财政投入,保障工读学校正常办学条件,完善少年教养所制度。这不仅是对潜在社会危害行为的有效规避,更是对迷途未成年人最大限度的挽救。
延伸阅读:
- ·教育蓝皮书:未成年人犯罪受家庭因素影响(2015-04-21)
- ·最高检出台八项措施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2015-05-28)
- ·兰州市对上半年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进行测评(2015-07-05)
- ·护航青春 致力未成年人帮教工作(2015-07-29)
- ·未成年人监护干预任重道远(2015-11-25)

 护理专业
护理专业  多媒体制作
多媒体制作  铁路工程测量
铁路工程测量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铁道类专业专题
铁道类专业专题  幼儿教育专业
幼儿教育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