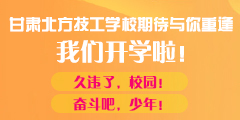图为梁思礼
梁启超九个子女,各个菁秀,其中三个成了院士。梁思礼被叫做“老白鼻”,这是父亲梁启超对他的昵称。风趣的父亲将英语Baby(宝贝)一词汉化,变成属于梁思礼特有的甜蜜。也正是这个“老白鼻”,后来成为我国航天质量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
回忆中的1949年,吹去历史烟尘,露出一绢恒久的画面,镌在如今91岁的梁思礼的心头。
1949年9月的一天,“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一如往常,驶出旧金山港,船上的梁思礼,刚从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和船上同样学成归国的20多位留学生一样,游子心念,归心似箭,千里之遥,快马一鞭。
天津的码头上,阔别八年、白发苍苍、眼角噙泪的老母亲迎接自己,正如饱受苦难的祖国张开双臂欢迎海外游子的归来。
几个月后,著名航天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6年后,钱学森回国,乘坐的也是这艘船。有人说,“克利夫兰总统号”为中国的“驯火史”带来了最初的火种。
火箭如喷着火舌的莽兽巨龙,梁思礼这些第一代中国“驯火人”就要为这头巨兽套上笼头,绑上马鞍,驾着它从战争的废墟驰向航天的大门。
爱国的“胎记”
一双大眼,鹅銮式的宽阔前额,一张典型的“梁家嘴”,举手投足间处处是父亲梁启超的影子。“像,太像了”,曾经在南开中学听过梁启超演讲的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见到梁思礼时,竟有种恍若隔世之感。
梁启超的遗传,一个留在了脸上,一个种在了心里。
有人曾经问梁思礼,你从你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说:“爱国。”
“爱国救国”几乎是梁家九子女的胎记。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有一幢白色的意式建筑,这里就是饮冰室,梁启超伏案奋笔之所。他在这里写的“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来的路。回忆中,梁思礼眯起了眼睛:“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属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
1941年,梁思礼赴美国深造。为了省钱,他曾裹着大衣在零下40度的储物室挨了一夜,险些冻死,也曾在罐头厂靠着冷冻豌豆过了一个暑假。尽管条件艰苦,但仍没有磨灭他心中“工业救国”之梦。为了能够转入“工程师摇篮”的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他放弃了嘉尔顿学院的优厚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1949年夏天,他拿到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著名无线电公司RAC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千金马、五花裘”无法稀释他的赤子热血,他选择了回国。
此时,他的同窗兼好友林桦,与他分道扬镳,留在美国。曾经朝夕相处的两人,人生的境遇由此画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抛物线。
几十年后,林桦成了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梁思礼成了航天部的总工程师。林桦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梁思礼住在普通的单元房里,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
有人问他对此有什么想法,梁思礼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祖国的。”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美国人嘲笑“中国只有子弹,没有枪”,认为中国没有运载工具,不承认中国是核大国。中央专委决定改进中近程导弹,进行“两弹结合”的热实验,梁思礼负责控制系统设计。
正当梁思礼埋头实验时,“破四旧”运动波及到梁家。在特殊年代,“梁启超之子”带给梁思礼的不是荣耀和尊重,而是数不清的磨难。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母亲卖掉家中老宅攒下的积蓄,成了梁思礼被揭发有经济问题的“证据”。一边唱着“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一边却被剃光了头发,坐在铺盖卷上,绝望地等待着去坐牢,梁思礼心里五味杂陈。然而,弄人的造化似乎不愿轻易放过他。1968年,母亲去世,梁思礼要去奔丧,却被要求“划清界限”;1974年,本该在运载火箭上大展拳脚的他,被下放到河南做了猪倌……
有人为他的遭遇鸣不平:“如果你不是1949年回国,而是1979年回国,或许就能躲过这些灾难和痛苦。”
他引用了哥哥梁思成的一句话作答:“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
梁思礼和所有的中国“驯火人”一样,站在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到他们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是戈壁滩上被漫天风沙遮蔽着的群像背影,他们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们的名字,被一笔一笔刻在历史坐标上。

 护理专业
护理专业  多媒体制作
多媒体制作  铁路工程测量
铁路工程测量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铁道类专业专题
铁道类专业专题  幼儿教育专业
幼儿教育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