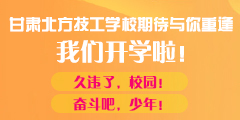一年毕业典礼上,一个腼腆的女生红着脸问她:“是不是我把一只角膜捐给您,您就能看得见?”
“谢谢你,好孩子,老师的病不是角膜的问题。”
小女孩想了想,又抬头说:“那我就把一只眼球给您吧。”
说起这件事,一直微笑面对记者的刘芳突然红了眼圈。
她只是贵州农村中学一名普通女教师,为什么被称为“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在她平凡的人生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平凡的故事?
从光明到黑暗
2007年,刘芳曾反复做一个梦:夜晚,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一抬头,忽见满天繁星。她抓住身旁的人,奔走相告,说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
那时,她刚失明。
十年前她就知道,这一天终将到来。原来她有点夜盲,到1997年,眼前晃起了“水波纹”,银色、金色、蓝色的光圈,宛如一朵“恶之花”,层层花瓣不断绽开。她看世界像是隔了一只鱼缸。
一纸命运判决从天而降——不治之症。
医生说,这叫视网膜色素变性,发病率只有百万分之一。
腿一软,刘芳险些瘫倒。
那年她26岁,在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刚工作四年,跟相爱的人结了婚,8个月大的儿子在襁褓中咿呀学语……
夜深人静时,她咬着被角,在黑暗中哭泣。
她曾是个快乐单纯的姑娘,苹果脸,身材娇小,人还没见先听到笑声,绘画、写诗、书法、唱歌、跳舞样样都行。
她喜欢教书,而且教得别出心裁。批改作文,写评语前先画个卡通脸谱表明整体印象,笑容灿烂的、一般微笑的、嘴角紧绷的、瘪着脸的、痛苦扭曲的,有的还顶着鸡冠子、留着羊角辫……这样的轻松幽默,学生们看得笑逐颜开。
失明了,还怎样画出一个笑脸?
她专门去学了两年绘画,希望用画笔留住这个缤纷的世界。画得最用心的是一只猫头鹰:黄褐相间的羽毛,站在枯枝上,背景是湛蓝的天空,最动人的是那对眼睛——又圆又大,仿佛能看穿一切黑暗。
视野一天比一天变窄,视力一年比一年模糊。
2001年,她读了最后一本纸质书,是《笑傲江湖》。
2006年,她看到的最后两个字,是课本封面上的“语文”。
2007年,她完全被黑暗包围。
当年一段录像保存至今:学生都放学了,刘芳从讲台上拎起包,摸索到门口,回头望了一眼她已看不到的空荡荡的教室,缓缓带上了门。
在黑暗中抓住光明
初见刘芳,很多人不相信这是个盲人。
在家,她扫地、洗衣服、倒开水、冲咖啡、炒菜、在跑步机上锻炼,动作熟练得几乎与常人无异。借助盲人软件,她发短信比很多明眼人还快。在学校,她可以独自走近百米,下两层楼,转5个弯,轻松找到公厕。
很少有人了解,这些年她是怎样挺过来的。
2008年初冰雪灾害时,小区停水停电,她拎着大桶,摸索着下6楼去提水。巨大的冰坨子在头顶摇摇欲坠,天寒地冻,一步一滑,最后她累得晕倒在地……
不知多少次绊倒、磕伤、撞墙、烫出水泡、碰碎杯子,现在她小腿上还满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绝望、沮丧、灰心,她想过放弃。但转念一想,又释然了:“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生活不能改变的话,就改变生活的态度。”
更令人称奇的是,她的班级成绩不仅没有退步,反而教出了两个语文单科中考状元,在白云三中至今无人超越。
有人建议她病退或休息,她婉拒了:“那样我的生命就真的终止了。”
一个盲人要想留在讲台上,无疑要付出超过常人几倍的努力。
写板书,她有时会写歪,有时重叠到一起。一次,没留意走到了讲台边缘,一脚踏空,摔在垃圾桶上。学生奔过去扶她,说:“最后两个字都写到墙上去了。”
多年以后,她的学生说:“刘老师歪斜叠加的板书,是我们青春记忆里最美的画面。”
眼睛沉入了黑暗,唯有心能抓住光明。
她尚未全盲时,有一次学生们发现,刘老师把课本拿倒了,照样侃侃而谈,这才知道,她根本没有看书,而是在背诵课文。
为了教好书,刘芳把初中三年的文言文全部背了下来,其他重点、难点也一一记牢,把几大本厚厚的讲义全都装在了心里。视力越来越差,课却讲得越来越精彩。
说、学、逗、唱,她几乎变成了相声演员,课堂上充满欢声笑语。“眼睛不好,上课就一定要生动,才能把几十双眼睛吸引到我这儿来。”
她用耳朵批改作文。学生朗读,她和全班同学一起即时点评。
“感情再充沛一点!”“他这个角度大家想到没有?”她像个乐队指挥一样调动着全班。
“该我了!”“我有不同看法!”学生们热烈响应。
听、说、读、写,多种训练同时进行,比单向的教师批阅效果更好。
学生越来越喜欢她。听说她可能不再担任班主任,学生们跑去求校长,哭着说:“一定要把刘老师留下啊!”毕业了,他们把自己的弟弟、妹妹牵到刘芳手上,点名要进她的班。
打开一扇心之门
2009年的一天,年轻老师章玉嘉向刘芳求助,声音都颤了:“我们班有个女生想自杀。”
找到那个女生,刘芳一伸手,摸到了纤细手腕上厚厚的纱布。这个平常很文静的小姑娘来自一个重组家庭,她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刘芳用一块布蒙上她的眼睛,说:“你就这样跟着我一天,试试我是怎样生活的。”
一天之后,刘芳问:“容易吗?”
“不容易。”
“我天天都是这样生活的。我都能好好活着,你有眼睛,又漂亮又可爱,完全可以比我活得更精彩,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呢?”
姑娘的眼泪大滴大滴落在刘芳手上。
刘芳又去姑娘家家访。她看不见路,只能让章玉嘉牵着自己。天黑了,她们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又深一脚浅一脚走过狭窄的乡间小道,数着电线杆,才找到那个偏远的村子。
刘芳告诉家长,孩子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一点爱。她把母亲的手拉到了女儿手腕的伤疤上:“你不爱女儿吗?”
“爱。”质朴的农家妇女一辈子都没有这样袒露过感情,而当“爱”字出口,尘封已久的心门终于打开了,母女俩抱在一起,痛哭失声。
从2008年起,校长何代乾交给刘芳一份开创性工作——心理咨询。那时,贵州农村学校的心理辅导基本是空白。白云三中地处城乡结合部,青春期与社会转型期交织,千余名学生心理问题丛生。
刘芳把自己的工作概括成四个字——用爱倾听。
在她建立的“成长档案袋”中,学生塞进了各种各样的纸条,把不愿告诉别人的“秘密”向刘芳倾诉——“我无法克制住对她的好感。我的心总是上下浮沉,不知如何是好。”或者,“今天,最疼爱我的奶奶去世了,我想坚强一点,可是怎么也止不住泪水。”还有,“现在的父母对我恩重如山,但我渐渐长大,突然很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去……”
让一个盲人去宽慰明眼人,这的确很少见。不过,任何人面对一个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柔弱女子,再难的事也该想通了吧?
一次,一个陌生人因感情挫折想自杀,错把短信发给了刘芳。电话打通了,她劝导得小心翼翼:“你只是一朵早开的花。有没有意识到,现在的你,其实不是你自己?”
前后三个月,刘芳一次次跟这个不曾谋面的姑娘通话,终于,姑娘有了笑声:“刘老师,我答应你,好好活着。”
刘芳不止一次收到这样的留言:“是您,在我心里点亮了一盏灯。”
那些穷孩子,那点滴的爱
记者采访时刚过中秋节,刘芳讲了一个月饼的故事。
有一年,她布置的作文是《中秋感怀》,男生陈祥写道:“中秋节到了,每个人都在吃着月饼。而我却不知道月饼是什么滋味,甜的?酸的?看到很多人不爱吃,把月饼丢在了垃圾桶里,我好想捡起来吃了。”
刘芳读得心酸,就去他家家访。父母在外打工,他跟老人住在破旧的农家小屋里。刘芳听到窗户上的声音有点奇怪,一摸,连玻璃都没有,几片塑料纸在风中飘摇。第二天,她带给陈祥一块大月饼。
男生咬了一口,噙着泪花说:“刘老师,月饼是甜的。”
很多年后,陈祥工作了,打电话要请老师吃饭。刘芳笑了:“你喜欢吃什么就带我吃什么吧。”
停顿了一秒钟,陈祥说:“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月饼。”
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大省。学生全部来自农村和进城务工家庭的白云三中,贫困生很多。对穷孩子,刘芳总会多尽一分心力。
有个自幼失去一条腿的残疾男生,刘芳承担了他初中三年的学杂费,又攒钱帮他安假肢。一个中档假肢相当于刘芳半年的工资。没料到,这引发了“爱心接力”。一位干部听说此事,要求共担费用。没多久,假肢厂厂长来了:“我免费给孩子量身订做一个高级假肢。”
终于能双脚走路了,男生跑来找刘芳:“我能不能叫您妈妈?”
叫她“妈妈”的学生不止一个两个。
不久前的教师节,已大学毕业也成了一名老师的袁凤梅发来短信:“刘妈,感谢命运中出现了您。”
读初三时,袁凤梅的父亲病逝,刘芳把她当女儿来照顾。袁凤梅回忆:“我最难的时候,刘妈始终陪在身边。她很少触碰我的伤心事,像阳光一样包容着我。”
中考前,刘芳抱着袁凤梅问:“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要相信女儿。”袁凤梅说,“你眼睛看不到了,还把我们教得这么好。我有什么理由学不好?”
那一点一滴的爱,在孩子们心里留下了长久的温暖。
一个孤儿在日记里写道:“刘老师,初中三年以来,一直都是我们全班四十几个同学看着您的一切,可是您却看不见我们的脸。您只能用心去体会我们对您的爱,用声音来辨别我们是谁。我好想为您做点什么,但是我一个孤儿想做却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为您祈祷,希望有朝一日,您能复明。”
有遗憾,更有爱和力量
曾祥雷,刘芳的一个终生遗憾。
那是个有梦想的男生,喜欢音乐和美术,曾经在一篇随笔中写道:“有人说,人生是一片大海。我认为在这茫茫人海之中是一片音乐的海洋,它在唱着生命的交响曲。”
但他初二时辍学了。在这片贫困的大山里,学生常常很小就跟着大人出去打工。刘芳和同事们家访的一个经常内容,就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家长,让孩子重返课堂。
刘芳把曾祥雷找回来,对他说:“先把书读好,才能更好地追逐梦想。”
学校里有个学生意外丧生,刘芳特意选曾祥雷代表班级去送花圈。这个敏感的男生懂得她的良苦用心,在另一篇随笔中写道:“刘老师是为了让我珍惜生命,不要做一些无意义的事。”
初中毕业后,曾祥雷又读职高,如愿找到了工作。
刘芳没想到,她可以扭转青春期的任性,却无法战胜根深蒂固的贫穷。
2011年的一天,刘芳的手机响了,听到的是一位母亲的哽咽——
曾祥雷死了。
他去架桥工地打工,在一场事故中,从40米高处跌落下来。
整理遗物时,人们发现一封还没来得及寄出的信,两页纸,写于他死前一周,是写给刘芳的:“我一次次逃课,您一次次把我叫回来,一句都没有骂过我。现在工作了,很开心。但每次想到您眼睛不好,我就很难过。等我挣了钱,一定帮您治好病。我就是您的儿子。有什么事情,您喊一声,我就会来的……”
这,是人们所知的他最后一个愿望。
刘芳的另一个遗憾是儿子。
她最后一次看清儿子阿牛的脸,他才七八岁,现在都读大学了。尽管能摸到儿子的鼻子、嘴巴、胡茬儿,她却只能想像,他长得帅不?黑不?她遗憾没能亲眼看到儿子的成长,更遗憾没能给儿子像其他妈妈那样的照顾。十多年来,关于儿子的每一缕记忆,都伴着甜美与刺痛。
才3岁,阿牛就会说:“妈妈不抱,宝宝自己走。”
从五六岁起,他每天早上都是先送妈妈上班,自己再上学,风雨无阻。
那时在白云区,常有人看到这个场景:一个小不点的孩子牵着妈妈的手,左右张望着过斑马线。有车,他就说:“妈妈不要动。”可以过了,就喊:“妈妈快跑快跑快跑!”
刘芳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在母亲搬来同住之前那些年,刘芳都是独自带孩子。因磨砺而早熟的孩子,对妈妈有着更深的爱。
“我妈妈是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做了很不平凡的事。”在小学作文中,阿牛写道,“她的眼睛看世界是黑暗的,可她的心在什么地方都会发光。”
自打刘芳坚持站在讲台上,就非议不断:“一个盲人,还教什么书啊?”但她有一种倔强的自尊——压力越大,越要站得直!而来自身边的爱和支持,则是她的力量源泉。
很多同事都当过刘芳的“秘书”,帮她打印资料、整理教案,领着她去吃饭、逛街、聊天。学生们都争着去搀扶她,把她牵到讲台上,还把粉笔、黑板擦放在固定位置,这样她一伸手就能拿到。
她的善良、乐观与坚强又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有个同事的女儿要做手术,血浆不够,她第一个报名献血。全校师生都知道她的存折密码,谁有急需都可以借用。
“刘芳给我们很多力量。”同事毛艳红说,“她都认真地活,我们有什么理由随便过?”
一条河流奔腾不息
刘芳爱读书。
甚至失明之后,她也常去逛书店。打开一本书,把脸埋进去,深深吸一口,当墨香弥漫胸腔,那字字句句就仿佛飞了出来,如萤火虫般环绕着她,让她沉醉不已。
她小学五年级写了第一首诗,后来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小作品。电脑装了盲人软件后,经常敲点东西就成了她最大的乐趣。令人惊叹的是,她先后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17万字,一部28万字,其中一部已经出版。
2011年7月,她和一些年龄相仿的同事去外地参加培训,闲谈间,大家谈起了共同的青春岁月。有人随口建议:“你也写写我们的青春呗。”
那一晚,她失眠了,十几年人生风雨如海啸般涌上心头。一张张远去或变老的面孔,一群群来了又走的学生,校园里每个角落,大山里的偏远村庄,那些欢笑,那些泪水……一桩桩、一件件,像是得到召唤一样浮现脑海,让她心潮澎湃,血脉贲张。
回到家,她打开电脑,一口气写了两千多字。此后,在教课、做家务、督促孩子写作业的间隙,她每天坚持写作,顺畅时一天能写5000字。
万籁俱寂的夜晚,她盘腿坐在小桌前,手指轻触贴着特殊标记的键盘,听着读字的机械之声,一路敲下去。黑暗里似乎打开了一个舞台,故事轮番上演,如河水般奔流不息。她要做的,就是把它们记录下来。
这部历时8个月写成的《石榴青青》,80%以上的内容是真事——一群“70后”年轻教师坚守西部农村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
这本书色彩明丽、幽默风趣,很多细微观察比其他作家更敏锐。
海伦·凯勒曾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记述,一位明眼朋友在树林中穿行了一个小时,却说“没看到什么特别的”。而对她来说,一块树皮、一朵花、一只小鸟的跳跃、一股小溪的清凉,都那么美,像“一场极其动人而且演不完的戏剧”。
刘芳深感共鸣:“明眼人总以为世界的千姿百态是理所当然的,只有失明之后才懂得珍惜。”
“比如灰尘。”她说,“很多人抖被子、拍枕头,都抱怨‘好大的灰呀!’对我来说,每一颗灰尘都是有生命的,跳跃在记忆之中。以前在阳光中看见灰尘,从没注意过它们,现在灰尘随风飘动的样子却令我神往。”
很多曾被忽视的细节,写作时竟历历在目。
那些搞怪、尴尬的场景,让她忍俊不禁;那些求知若渴又困苦无助的孩子、那些美景与贫穷交织的山村、那些因生活重压无奈离去的同事,让她笔重千钧。
2011年4月的一天晚上,敲完最后一个字,刘芳仰面瘫倒在沙发上。心绪从主人公感伤的世界里缓缓退潮,归于平静,像漂在一片平缓的河面上随波逐流。她仿佛重过了一遍人生,如今只剩灰色“水波纹”还在眼前晃动。而顶灯在眼皮上照出的光晕,像新的希望在远远地召唤。
在小说的前言中,她写下一句话:“一条河,在地面奔腾时是一条河,在地下流淌时还是一条河,最后它们都奔向了大海,在那里它们的灵魂是平等的。”
延伸阅读:
- ·刘芳:把撕碎的命运一点点拼起来(2015-12-03)
- ·“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刘芳独白:我是谁?(2015-12-03)
- ·刘芳:与教育热恋,学生都是她的眼睛(2015-12-24)
- ·刘芳:用心底的阳光驱散眼前的黑暗(2015-12-24)
- ·刘芳:失明教师的课堂照样精彩(2015-12-24)

 护理专业
护理专业  多媒体制作
多媒体制作  铁路工程测量
铁路工程测量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  铁道类专业专题
铁道类专业专题  幼儿教育专业
幼儿教育专业